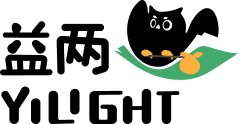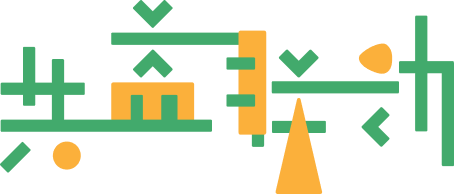访谈开始之前,我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的阅历有很大差异。正式访谈后,我却很开心。第一,我真正了解到了草根公益人的出发点和坚守,从馒头到搬家,木兰人彼此都投入了许多。第二,专业背景与否或许不是必备,关键在力求改变的决心,丽霞与木兰们始终围绕着女工们的需要,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三,丽霞在过程中发挥了许多女性特色,有效动员了更多群体参与到她倡导的行动中来,比如隐身的爸爸们。 如果你对女性发展、公益小白成长感兴趣,丽霞的分享可以带给你参考。
——访谈人 陈茜
应南琴:木兰花开的创始人和员工可能都是流动女工的身份。对流动女工的需求、困境都比较了解。木兰花开在开发各种项目的过程中,有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探索?
齐丽霞:项目一直会有发展变化,但是也有一些项目是我们很强烈认同的、一直不变的。
文艺活动是我们持续在做的,因为我们有几个功能寄托到文艺活动身上。第一层次,从需求来说,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是每个人需要的,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是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二层面,从社工的角度来说,文艺活动实际上是给人赋能的。通过参与文艺活动,她(指流动女工)从不敢、不能,到敢、可以,到很胆大,甚至到鼓励别人,她的个人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是一步一步提升的。
可能对大家来说,到这个地方参与文艺活动已经很有收获了。但从机构层面上来说,我们还会引导我们姐妹说,我们参与文艺活动不止于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发声,发出群体发声。我们每个人发声了,就是群体的声音。那我们也说,我们不替谁表达,我们鼓励每个人能表达,表达多了声音就出来了。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声音也是多元的。不是说群体的声音都是(整齐)划一的。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精神状况不一样,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每个人想说的。我们给大家包容和接纳。我们不会说,诶,她特别能说,她文化程度高,她表达的就是唯一的、对的,没有!我们接纳每个人的现状,每个人这样说有她背后的理由。

姐妹们的排练
应南琴:我接触木兰花开的时候也特别被这个理念触动,就是让流动女工自己发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有很多代替服务对象去发声的情况。当然更好的还是能够鼓励流动女工她们自己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这点也是我一直认为木然花开很珍贵的一点。我有点好奇,这个理念是您在和联合创始人最早在探索的时候就提出来的方案,还是在后面摸索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齐丽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坚持做事,去想大家的需求。
前期我们做得有一点影响力、被看见的时候,有一些媒体来采访我们。采访之后,我们发现不是我们想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探讨“被表达”跟“我们自己表达”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多地去坚持自主表达,自主发声。我们不要被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努力去创作我们自己的原创。
我们周边的文化中,跟女性相关的歌其实是有一些固化的(表达),非常多的歌曲甚至完全没有性别意识。我们不反对每个姐妹喜欢任何流行歌曲,你平常想咋唱咋唱,我们自己开晚会、去KTV玩,你想唱《爱情买卖》、《香水有毒》,随便!但是参加我们文艺对外表演的时候,一定是要表演我们的原创作品。我们不在意唱得跑调不跑调,唱得齐不齐,这个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讲出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应南琴:您刚刚提到说一些歌曲缺乏性别意识,木兰花开的姐妹们也希望通过自我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您可以具体举些例子说说一般的流行歌曲和姐妹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在表达上的区别吗?
齐丽霞:我刚才正好也提到两首歌《香水有毒》和《爱情买卖》,还有《小苹果》。唱得那个大街小巷啊……我就搞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火!但是谁都唱,谁都会哼。但是这里面的歌曲表达,你稍微一分析,它其实真的是又不平等,然后很多的隐忍跟屈辱都在内。
以我们的歌曲《不完美的妈妈》为例,在这里面我们探讨妈妈的身份。是不是你从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你这一生都是妈妈?有没有可能在“妈妈”之外,你自己想做什么事,想要去什么地方?有人说,虽然我没钱,但是我还蛮喜欢旅游的。有一个常年不见她穿一件漂亮衣服的女性,她说,我其实没结婚的时候特别喜欢穿裙子,我那裙子多漂亮!但是从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再也不穿裙子了。因为不方便做家务,不方便抱孩子。你要是不和她细聊,你会觉得这个人从来不穿裙子,她不爱穿裙子。但其实她有她女性化的一面。也有挑战她的原来生活状态的女性,让人想象不到的。比如有人说,我特别喜欢打拳,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学打拳。

《不完美的妈妈》演出现场
在讨论做不做妈妈过程中,我们也去挑战大家:如果一个女性不做妈妈,你们会不会指责?有人说,那如果她不能生,那也没办法!那我们就不指责她。进一步地,我们就问:如果她能生,但她不想生呢?这个问题在基层女性里面是不被当成问题的,也不被讨论的。大家会觉得,她怎么可能能生但不想生呢?这时我们提出来:就有人这样!比如考虑事业发展,害怕容貌变形,或者就是没准备好,她不想生,行不行?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很激烈的讨论。有一派就觉得不理解:那不行,女人都得生孩子!也有一些人觉得:那是她个人的事。我们为什么管呢?我们为什么要指责呢?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把这一句话加上: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
有很多人跟我说,你们的歌好前卫呀!实际上是在创作过程中跟大家探讨,去挑战传统的想法。那这个歌曲背后就有了性别平等的意识,有了对女性的自我发展,自我被看见的表达。在讨论之前,很多姐妹都认为:我是一个好母亲,因为我能牺牲,我能伟大。什么好吃的我都不吃什么,家里的钱有多少,我都给孩子、给老公,我才是伟大的。其实它的反面是:当一个女人做不到的时候,她会自责,也会被别人责备。我们就要把这个地方给打破!你不这么做你就不伟大了吗?当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那大家其实就不会陷在这个传统意识的圈里,我们才比较能去往前讨论女性的自我发展。
应南琴:因为“流动女工”的身份里面有一个“流动”,有一个主流的想法是说希望孩子和流动女工都能够融入当地社区。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想法?在流动女工从一个是原来自己生长的地方流动到大城市发展的情况下,跟当地社区的发展是否有一些张力?怎么去应对这些张力?
齐丽霞:从社区融入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从人数来说,以我们所在这个城中村为例,本地人不到两千人,外地人,即便是在这两年因为各种原因有所减少,也有两三万人。一滴水要怎么让一杯水融入?我们有一杯水,我们要融入到河水里面,我们要融入到海水里面,很容易。但现在是反过来了,你让更多的人融入(一小部分人)是不太可能的。从逻辑上来说就说不通的。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融入应该是“融合”,就本地人跟外地人融合。那这个“融合”它就得两边都有意愿,ta们互有需求,要融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更好的社区,为了更好的美好的生活。但目前都没有这个意愿。本地人我收房租就好,我跟你融合干嘛?然后外地人,过三五年,我就走了,我跟你融合啥?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暂住地,我没有任何权利。比如说,社区工作,这么多外地人我们觉得社区哪个地方不合理,我们要去动手改变,你是没权利改变的。早些年,我们想在不同的地方放点垃圾箱,本地人不同意你就放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不管谈社区融入、社区融合,我都觉得,没办法谈。 我们(的地方)叫社区中心。大家对我们这个叫法会有一个印象,(以为)我们在做很多的社区工作。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更狭义地指:我们这个活动室是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背后我们能做的,我们想做的社区工作根本做不了。但你做社群工作还行。我们跟个别的本地居民关系也不错,本地的儿童和女性参与活动,我们都欢迎都接纳,甚至我们还得注意一下ta们的感受。
应南琴:对于流动女工来说,她本身有“女工”的身份,也有“流动”的属性。在城市生活过程中,这个流动属性会不会给她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在交互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张力?换一句话说,您觉得流动女工和只是留在本地发展的女工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齐丽霞:从心理层面,她(流动女工)一个地方哪怕是住十年以上,她没有归属感。她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她的家。从外部表现上来说,比如说她的出租屋里面,她很难做规划,也很难从长久来说我需要什么,大家都会有一点将就。如果是留在本地的,你比如说她的房屋要干嘛,特别重要的家具之类的。这个是不同的。因为大家心里就会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一样。 那你说这个特别的需求的,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群体性的特别的需求。因为它放到不同的女性身上,似乎也都说的过去。比如说自我成长。流动女性、留守的女性,甚至不同阶层的女性,都想自我成长。但是在当时的局限下,面对的职业困境只是程度不一样,其实都面对。只是可能受过更好文化教育的,她们意识到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基层的,不管是流动、留守,在我看来是一体两面,并不是说流动女工就是流动女工,极少数是只留守从来没流动过。我们聊过,大部分的可能她是阶段性地,这个时候是流动的,那个时候是留守的。我在家里带几年孩子,然后我又出来了。所以从动机的角度来说,她们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面对的困境都是自我意识不强,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地位受传统的性别的压力和禁锢。“压力”有可能她自己想怎么样但是不能怎么样,“禁锢”有可能是她自我都认同了。有一些妈妈,孩子已经大了,她想找工作,老公就不让她找工作。当她很想找的时候,这就是个“压力”。当她觉得我不找工作挺好的,我就在家照顾孩子,给ta做做饭也挺好的,那这就是对自我发展的一个“禁锢”。我会觉得在留守的女性里跟流动的女性里都有。
我不太确定更高阶层的女性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同样的,还是是同样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这些女性受到的压力跟反抗不一样。以家暴为例,有一些文化程度甚至收入特别高的女性,她受到的家暴,在家暴背后被禁锢,她自己走不开,那个程度跟一个基层的女性好像差别并不大。我们2019年做《生育记事》,在对外去演出的时候,非常多的相对来说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女性,她们看到的那种感受,其实是跟我们是特别相通的。

木兰花开的团体工作坊
应南琴:我一直认为不管是教育文化程度高低或者经济实力高低,面临的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固有印象固定思维都是相同的。如果经济实力强一些的话,相对自我发展的资源更多一点,也能获取更多支持。但可能流动女性获得的支持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木兰花开在提供支持这一块也是特别重要。
齐丽霞:我们是这样的,就以培养姐妹骨干来说,经常是这些姐妹各方面能力都已经发展了,然后她离开了。那我们再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再来新的姐妹,我们就重新培养。像《生育纪事》,很多人问还能不能再重新演出?我们说,不能重新演出了,只能再重新排一出。因为当年那些姐妹已经真的都天南海北了。
我们觉得这也有好处,好处就是这些姐妹就像一朵木兰花一样,开花结果飘落到他乡、他地,把我们想传达的观念、想传达的理念去传到别的地方。我们根据她们自身的行为,给她们寄书寄、资料、寄我们的文化衫,让她在当地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我们这边给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这都是在双方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因为木兰也一直很艰难。

木兰花开的姐妹们
在这个艰难情况下怎么给对方力量?那我们这些姐妹去到不同的地方,也能做到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一个姐妹说,我们住那个地方,我觉得有人是在打老婆,是不是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打电话问我们,这个可以怎么办?我就给她寄反家暴手册。我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啥时候跟她碰面?要是不行了,你能不能把这个书塞到她家门缝下面?总之你让她知道有这个可能性:第一,不管是打孩子、打老婆,让她知道有可能是犯法的。要是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被家暴的人接到(手册),因为后面有联络地址,严重的时候她至少是可以有求助的途径。不然有些人就没有。那回到乡村的,我们反家暴的这些(宣传),就在她们那个村里头贴的哪儿都是。就我们让她们去贴。流动性带来的好处就会有。因为流动性,她认同之后,她的观念可以传递。就力所能及,她能做到什么,我们也不要太强求。
访谈:陈茜 应南琴
文字:陈茜 应南琴
图片均由齐丽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