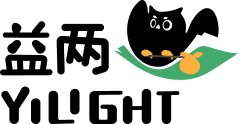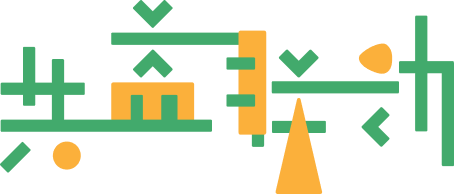访谈人:非常开心能够请到阿强做我们这一期的益两300计划的嘉宾!在我们访谈开始之前,能不能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胡志军: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分享。我叫阿强,全名胡志军。我之前创办的组织叫 “出色伙伴”,原来叫同性恋亲友会,现在我还在以理事长的身份做一些机构工作。
访谈人:您刚刚说到同性恋亲友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你们选择了同性恋的亲友这个群体,因为我们周围很多的LGBT朋友会更多地关注ta们自己的权益,比如ta们自己有没有被认可,ta们自己能不能过上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等等。那么您是为什么决定在LGBT领域从事这样的工作呢?又为什么会选择同性恋亲友这类群体为服务对象呢?
胡志军:我其实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探索。我最初开始关注LGBT领域时,大多数组织都是从防艾滋病的角度切入,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那时,很多组织都是通过热线服务和外展等方式来服务LGBT社群的。初期我也从事这些工作,但随后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而且我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我发现,我周围许多LGBT人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家庭的不接纳和父母的“催婚”。在中国社会,我们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十分紧密,而外部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会很关心。我们无法逃避父母不断询问“你何时结婚”的压力。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正好到了适婚年龄,我的父母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让我深有体会。
随后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如何使中国的同性恋父母从担忧变为支持。与此同时,我的家庭经历也对我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长时间没有向父母坦白,当父母开始催婚时,我曾犹豫不决,或者因缺乏勇气和准备而拖延。但我意识到我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我告诉自己在30岁之前会一定要向他们坦白。然而,我母亲在2006年突然被诊断出晚期胃癌,生命开始倒计时。面对母亲,我内心陷入了挣扎,纠结是否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在她去世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这是我内心与自我的一场战斗。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告诉她,会不会显得我很自私?因为她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但如果我不告诉她,我会觉得我没有对最重要的亲人诚实。这段时间,我内心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和博弈。
直到我母亲在2006年夏天去世,我依然没有向她坦白。在她临终前,她专门叫我回到家乡安徽,因为在我们家乡,长辈在孩子结婚时会准备红丝带等物品。她将这些东西交给我,就像在告诉我她即将离开人世,她知道她的生命即将结束。这一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因此我意识到,如果我要针对LGBT群体做一些事情,我应该更加关注ta们的家庭。
对LGBT群体而言,家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一个接纳和支持你的家庭能够帮助你勇敢地做自己。同时,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无数家庭共同构成了社会。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接纳和支持自己的孩子,整个社会环境都将发生积极的变化。因此,我在2008年创立了同性恋亲友会,以此促进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访谈人:我可以理解,对于LGBT这些人群,家庭其实是离ta们最近的,是一个可以接纳ta们,或者说ta们可以坦诚面对的最小的单位。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一句话特别棒,就是家庭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的话,它其实可以反转为最强大的支持力量。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看法。就此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您在试图实现这样的反转的过程中,您做了哪些尝试,或者说您用了哪些途径?就是您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能够去促进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这样一个反转的发生呢?
胡志军: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和摸索的过程的,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十五六年里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的方向是没有变的——我们鼓励更多的家长站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的,这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同性恋不会跟自己的家庭分享,他们会觉得如果我跟我的父母讲的话,他们一定会崩溃的,他们会活不下去的,他们一定不会接纳的,很多同性恋都觉得这是“一定”的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这些家长站出来说,我接纳了我的孩子。当你在现场听到几个家长说他们已经接纳他的小孩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震撼感就让那些LGBT觉得,原来孩子出柜后这些妈妈都没有活不下去,她们还坐在那里好好的,而且父母接纳自己的小孩是可能的。最早很多家长在孩子出柜的时候会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同性恋,只有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想做这样一个所谓的变态是吧?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LGBT出柜了以后,家长看到了就会觉得,原来不是我自己的小孩一个人这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做这样的孩子的家长。
所以我们坚持的就是鼓励这些家长讲出他们的故事。早期很多家长还会觉得说我要去接受电视采访,我要去面对视频,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但后面我们不断鼓励他们让他们把故事说出来,因为如果只是自己在身边讲的话,不但会很累,而且也影响不到多少人,而如果你借助了媒体,那可能你影响的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从公益的效率上来讲的话这样明显会更有意义。
访谈人:阿强,我理解您做LGBT相关的工作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业或者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份收入了,那么您是怎么会把它确定成您的事业或者人生的方向呢?您是怎样看待这一份事业的?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您有没有过内心挣扎过呢?
胡志军: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我真正开始参与这个事情是2000 年。早期的时候通过接热线,或者做艾滋病机构的志愿者,帮公益组织做媒体传播,到后面创办同性恋亲友会。其实刚开始的几年里我也没想过要去做一个全职,那个时候我几乎看不到一个模式或者蓝图——就是一个 NGO 到底应该怎么做?由于并没有一个成型的组织做示范,所以最早三年我们都只有志愿者团队。
但三年后我觉得我们已经遇到瓶颈了,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走了。201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学习,后来我刚好就知道在国外有一个相关的组织提供实习的机会。我觉得那段实习让我打开了视野,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那里我亲眼所见研究性别的机构可以有几百个员工,可以服务很多议题,而且做得非常专业。我的亲眼所见和参与实习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非政府组织(NGO)的实力和潜力。在实习期间,我参与了多项活动,这些活动经历让我确信自己也有能力参与到这一事业中。这两个多月的实习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尽管之前我也有所犹豫,但这段经历为我增加了更多的信心,让我确信自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回国前,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经营原有的物流生意,还是放弃旧业,投身于这个新领域?在即将回国之际,我下定决心要投身于这项事业。为此,我转让了手中的物流公司,决定全职从事。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我的事业。起初,作为志愿者参与时,我虽然对此充满兴趣,但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我曾担心NGO是否意味着贫穷和艰辛,担心自己无法维持生计和照顾家人。然而,当我下定决心,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后,这些疑虑逐渐消散。我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事业,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对各种挑战。
在2015年,移动社交领域发展迅速。我看到一些同领域的项目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投资,这让我感到很心动。当时我也开始动摇,认为自己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我曾向一位投资人提出一个将移动社交与旅游相结合的创意,并向他展示了我的想法。他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承诺会为我提供投资。然而,当投资真正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犹豫了。我告诉投资人,我需要先去旅行一趟,等旅行结束后,如果我仍然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再接受他的投资。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考虑。
于是,我踏上了前往西北的旅程,乘坐火车十几天,从西安一路到新疆。在戈壁滩上,我看到了那些初生的草芽。那时大约是五月初,西北的草地上只有零星的草,尚未连成一片。这些草在广袤的戈壁上显得尤为单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所从事的事业就像这些刚长出的草,虽然还很脆弱,但已经有了生机。如果我此时放弃,那就像是放弃了这片尚未繁茂的草地。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不舍,几乎泪流满面了。我清晰地认识到,现在放弃就等于放弃了这片尚未成长的草地。这个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
回来后,我告诉投资人我决定继续从事亲友会的工作。虽然赚钱的机会很吸引人,但我认为也不一定会成功,而且我也不愿放弃这片还没长成的“草地”。投资人表示理解,他们也提前预测到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2017年,我们组织了许多活动,但在管理方面遇到了瓶颈和挑战。同时,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第一次申请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时,我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如机构内部的纷争、志愿者的不满等。因此,我决定从一线工作中抽离出来,去探寻更多的可能性。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习经历让我深入思考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意识到,无论是在管理还是其他方面,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然而,当我回国后,我充满了活力和决心,想要推动一些重要的改变。这段时间的发展让我再次充满了动力。有时候,人们真的需要暂时从手头的工作中抽离出来,否则每天面对的都是无休止的现实问题,这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当我回国后,我再次审视许多问题时,我的悲观情绪有所减少。我发现,社会活动家们往往都拥有一种“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他们总是盲目乐观地面对各种挑战。而我,虽然并不完全属于盲目乐观,但当我重新回到这个领域时,我也开始探索各种新的方法和可能性。
访谈人:我周围几乎所有的公益人,他们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挣扎或者矛盾,他们会觉得既然我在公益受到了那么多的否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商业的工作?当您在拒绝天使投资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张力或挣扎。每个公益人在其公益生涯中可能都会思考:我为何要如此辛苦?我为何不能去追求经济收益?实际上,除了公益,我也拥有高学历,有能力赚取高薪。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从您的描述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状态。所以我就想再追问您一下,您是否深入分析过自己内心源源不断的正能量究竟来源于何处?这种正能量是如何让您排除追求更舒适生活的念头,使您能够持续向前,不被外界杂音所干扰的呢?这种能量究竟源自何处呢?
胡志军:当然,我也并非始终充满正能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当我不在国内的时候,那是我修复内心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那段时间里,国内的事务主要由同事们负责,这使我得以从中抽离出来,进行深入的自我修复。当我回到国内时,我告诉同事们这时我的内心处于最健康的状态。现在,我在看待问题时,总是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当我遇到麻烦时,我会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思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以及这是否是我能够承担的最坏情况。一旦确定了我可以接受的底线,我就会开始寻找更好的可能性。好的可能性会如何?或者中间的那种可能性又会怎样?我是通过自我说服来寻找这些角度,并将事情引向更积极的方向,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点。另外,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即我的个性特点。如果遇到让我焦虑的事情,睡一晚后,第二天早上我就会忘记。我确实会面临挑战,但每当夜幕降临,仿佛那些内心的困扰就被阻隔了。第二天醒来时,那些冲击已经大幅消退,它们不再在我内心徘徊或困扰我。我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所不同,这是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另外,我的性格比较倾向于“兴奋型”,对于新事物和挑战性的事情我感到很兴奋。在职业相关的心理测试中,我发现我的抗压能力和持续坚持一件事情的能力都是满分10分。但如果要我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我可能只能得2分,因为我对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不太擅长,也不感兴趣。另外,我特别喜欢和别人聊天。当我遇到难题且没有解决方案时,我通常会列出三到五个人,然后找他们聊天。聊完之后,我觉得他们给了我新的视角,这通常会启发我。如果我接受了某个视角,我会用这个新的角度来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可以放下担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访谈人 :LGBT人群在很多时候会面临来自父母的误解和偏见,父母可能会质疑他们的心理状态,并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这使得心理咨询往往是发现问题的第一站,心理咨询专业领域内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判断的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对你们在这一领域目前所取得的效果和现状非常感兴趣。请问能否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改进措施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胡志军:关于心理咨询领域,早期在2013年,我们行业内发生了一起官司。当时,某心理咨询机构声称能够治疗LGBT,并明码标价一个疗程的费用。随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将此事起诉至北京法院。在此过程中,百度扮演了不当角色,因为在其推广中,只要机构支付费用,百度就会推广关于治疗同性恋的内容。最终,此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
最终,虽然百度并未成为被告,但那家声称能治疗同性恋的机构被判败诉,并需赔偿5,000元。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得心理咨询机构人员开始意识到,若他们不负责任地宣称能治疗同性恋,不仅可能面临法律诉讼,还需承担经济赔偿,从而认识到这是一个风险点。此外,中国众多心理咨询书籍甚至教科书存在大量错误内容。近期,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此现象。上个月,一名大学生分享了他们的心理咨询课本,其中仍提及如何治疗同性恋,采用厌恶疗法等方法。他指出了这些内容的错误,并强调我们需对这些课本和教材提出质疑和挑战,因为其中的观点本身是错误的。
2001年,中国第三版的精神障碍分类标准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剔除。然而,二十三年后的2024年,仍有书籍将同性恋视为问题,甚至被列为心理咨询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或必选课程。这种情况反映出心理咨询师行业培训的不系统性,部分早期受训者的观念尚未更新,他们可能在生活中也缺乏与同性恋群体的接触。因此,心理咨询领域在这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
在与心理咨询机构的一次分享活动中,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在交流即将结束时表示,他后悔没有早些邀请我们进行分享。他提到之前曾有一位15岁的同性恋少年,在其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他当时一直努力引导家长如何改变孩子,但若能早些与我们交流,他可能会更侧重于如何让家长接纳孩子。缺乏相关知识会导致处理方式和方向完全错误。他当时那种处理方式不仅无助于孩子,反而可能加剧其心理问题。咨询师在孩子眼中往往代表权威,而家长可能受其影响,认为孩子应努力改变。这种观念可能使孩子觉得自身问题源于不努力或不正确的选择。因此,我深深认识到如果我们能进行更多的分享并影响这些专业人士,将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当前,鉴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家庭开始养育子女,这些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访谈人:我认为您刚提到的内容极为重要。早期的心理咨询干预手段,往往聚焦于试图改变个体的性取向,然而这种努力通常是徒劳的。从您的描述中,我更倾向于看到一种以家庭咨询或家庭干预为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孩子、家人以及可能涉及的其他社会角色,如同事、孩子的朋友等纳入考量。这种群体式的心理干预模式,实际上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心理支持的方式。
胡志军:我们主要基于生活场景来推动相关服务,并回归专业角度。虽然我们不专门从事心理咨询,但我们的工作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在举办分享会时,我们采用了类似社工小组的方式,让参与者围坐一起,这种方式在社工小组中无论用于戒酒、戒烟还是其他目的,都证明是有效的。通过参与团体分享,人们能够获得能量,并乐于与他人分享。我们注意到,许多参与活动的人,在仅仅两小时的分享会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记得有些母亲在初来乍到时,因孩子是同性恋而痛哭流涕。然而,在倾听他人的分享后,她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有人质疑我们如何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改变。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帮助了人们面对和接受生活中的挑战。我经常在现场观察,发现刚开始时,父母坐在那里,孩子坐在椅子上,他们都不想正眼看这些同性恋者。这是因为他们是勉强来的,很多人觉得这种情况很棘手,不知道如何处理。有些人甚至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参加某些活动或聚会,担心他们会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当他们来到现场后,往往会发现这里的人都很体面、有工作和专业背景,这与他们的想象截然不同。在听取其他人的故事和经历时,家长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孩子并不孤单,而且他们的选择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这有助于消除一些家长的疑虑和担忧,让他们更加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孩子。
许多家长缺乏耐心聆听孩子的讲述,尤其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平等交流常未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当这些家长听到其他孩子分享经历时,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有些孩子分享自己在8岁时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这让一些家长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反思是否自己的孩子也是受到了不良影响。随着家长逐渐被故事吸引并产生好奇心,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这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观察到的情况。
中国的同性恋人口数目庞大,除了与性少数直接相关的人群外,他们也还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亲戚等。在参加培训后,他们开始反思并发现身边的亲戚也可能是同性恋。这显示出同性恋或性少数话题并非仅限于LGBT人群,而是每个人都应关注的社会议题。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与自己无关,但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身份,人们会逐渐发现身边的同性恋者。
我曾听说过,有人因家人对同性恋的负面评论而感到不悦。尽管他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未敢公开。这反映出许多人误以为同性恋与自己无关,但实则同性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美国,早期对同性婚姻的数据调查也显示,那些有亲人朋友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远高于那些没有此类经历的人。这进一步证明了真实的个人故事分享与权利平等之间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
访谈人:在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想请阿强描述一下您心中的或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有人说欧美国家状态很优秀,您是怎么看的?他们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
胡志军:欧美国家目前仍在努力应对性少数群体的议题,其中跨性别领域的进展尤其值得关注。尽管同性婚姻问题在某些地区得到了解决,但跨性别议题却逐渐凸显,引发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中,还涉及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欧洲各地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欧美国家距离实现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解决诸多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状态的达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我还是持乐观态度。与俄罗斯等基于宗教原因打压同性恋的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宗教反对力量相对较弱。从商业角度看,许多组织仍然蓬勃发展。同性恋个体的生活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他们正常地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享受生活。
同性恋群体所求的无非是平等权利,而非特殊权利。他们希望能够在社会中享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待遇和机会。因此,我认为只要社会能够理性看待同性恋问题,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和理解,那么这个社群就能够为社会和谐贡献重要力量。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并不认为同性恋群体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
访谈人:关于Z世代的人群,特别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意向参与LGBT相关的公益活动,您对他们有何期待或建议?他们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可能无法再拓展的某些领域,您认为新一代可以如何继续推进并取得进步?您可以他们提供一些鼓励的话语,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关于您个人的职业规划,如果您不再继续当前的公益事业,您是否有考虑过转向其他领域?除了公益和LGBT相关的事务,您最希望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胡志军:关于Z世代的小伙伴们,我深感他们已经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我们的传统框架。我们当前所用的框架,主要围绕着同性恋的成长脉络和全生命周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展开,然而,Z世代的人可能已经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与前面几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可能在小学就已经出柜了。00后这一代,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可能不再将“出柜”视为一个问题。他们可能会惊讶于,为何我们的前辈还与父母在“出柜”问题上纠结,为何还有那么多的挣扎。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相对年轻,许多家长的年龄甚至比我还要小,对于这一代家长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大大降低。
此外,这些孩子与父母的平等性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与家长的亲密度和平等性都非常高,这与我们那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当孩子们与父母分享他们的生活时,父母往往已经能够洞察到他们的内心。通过孩子的上网行为、与他人的交流,甚至眼神,父母都能判断出孩子的真实状态。这个过程与我们所经历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并没有能力去指导他们应该如何行动,我认为他们已经在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自己的理念了。他们的方法可能更加融入生活,或者已经不再将此视为一种责任。有些人可能已经活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觉得影响社会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活出了真实的自己。
当然,如果他们想要推动某项事业,组织化的发展或许能够带来变化。然而,组织化的发展并非易事,因为组织可能会迅速消亡。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因此,我很难给出一个成熟的建议。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曾思考过如果我不从事与LGBT或同性恋相关的工作,我会做什么。如果我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我可能会选择从事房地产销售,因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甚至已经准备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我也曾考虑过在其他国家创办与LGBT商业相关的事业,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例如,泰国现在越来越成为全球LGBT旅游的中心,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泰国对LGBT群体相对包容,甚至有可能在今年6月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环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LGBT顾客和游客。
结语
阿强是个擅长分享故事的人。当他讲到自己面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母亲也无法坦承自己性少数的身份时的挣扎与遗憾,当他讲到他在事业发展期考虑转行时,看到火车车窗外西北的戈壁上未连成片的野草,想到自己未竟的志业而潸然泪下,听众很难不为之动容。正如访谈中所说,阿强所倾力的公益事业虽然切实有效地回应了社会现实问题,但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坎坷的。但得益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努力以及阿强“打不死的小强”的乐观心态,他的事业得以延续至今。益两300团队希望,阿强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成熟的社群管理经验能够给大家参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