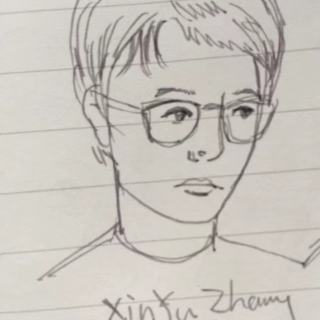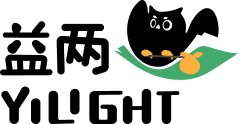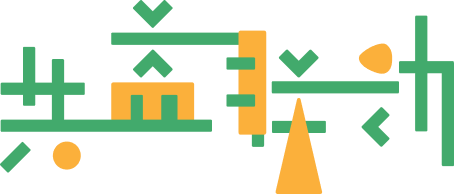我和新宇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她在广东绿芽工作,后来又知道她辞职,但从来没有机会坐下来认真聊聊新宇到底在做什么。2022年有幸开展“益两300计划”项目,新宇是我们的第一个访谈对象。
在访谈中,新宇讲述了自己是怎样误打误撞成为儿童性教育工作者。从北京到广州,新宇走遍了各个乡村深入实践本土儿童性教育,却在一次田野调查中对当前以“课程包”的形式推广“全面性教育”的儿童性教育模式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怀疑的驱动下,新宇离开了工作了多年的公益行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投身自己最初,也自始至终感兴趣的乡村妇女性别平等行动。但这一次,新宇的实践似乎又与我们普遍认知中的“乡村妇女赋权”相去甚远。
以下是新宇的讲述。
我好像只能做公益
公益圈儿,这个就很有意思。你做其他任何行业:考公务员、去银行、做土木、买房子……大家都不会问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只有公益人会被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份职业?”毕竟工资也就那样。有些工作赚不到钱,那至少要稳定吧?公益圈两头都不占,还特别忙。
我是05年上大学,09年毕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也挺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最初了解“公益行业”是在学校做乡村支教和残障儿童方面的志愿者。后来发现学校有社工系,就选修了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课程。大三的时候我接受了一些培训,了解了性别方面的理念和理论。也是从那时开始明确了自己将来的就业方向——想从事公益行业,特别想做和性别有关的公益项目。对我来说是挺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国内全职做公益的人不多,工资也不高。我跟父母谈,父母对我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父母都能支持你。” 这确实算是一个需要 check privileage 的事情——因为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所以我没有“生存”方面的隐忧。如果有一天真的被环境逼迫到不得不做,可能我就不会再去想自己喜欢做什么、更擅长做什么。
真的要说为什么选择公益行业……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好,也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你让我想其他的职业……去考公务员吗?或者去企业工作?我身边有很好的对照样板,就是我丈夫。他在民营企业工作。我和他的同事吃饭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也好,或者各方面,好像确实只能做公益,也最适合做公益。你让我和我丈夫的同事共事,我真是办不到(大笑)。这些职业,金融也好,建造也好,确实是在创造很大的价值,但我自己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误打误撞成为儿童性教育工作者
我的工作算是跨在两个领域之间:一方面是儿童性教育;另外一方面是乡村妇女赋权。在儿童性教育领域的实践中,我特别注重乡村妇女和乡村实践;而在乡村发展或者乡村女性这个领域,我又是一个做儿童性教育的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当时儿童性侵犯项目刚好缺人,机构就让我去做了这个项目,算是误打误撞成为了儿童性教育工作者。
其实我自己有段时间很纠结,觉得自己做的项目好像和性别平等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对比同事,她们天天都在搞妇女能力建设、小额资助、团队建设……每次我和她们一起出差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呐!这个才是真正的工作!”
后来就没那么纠结了,因为我逐渐把性教育当做一种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从娃娃抓起”嘛。我们做的性教育是“全面性教育”,其中与性侵犯有关的内容可能只占 5% -10%,主要强调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概念,强调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这和很多人认知中的“性教育”可能有差异,但这其实才是国内性教育行业大家真正在做的事。
2014年,我搬到广州,加入了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担任副秘书长。到了绿芽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乡村儿童性教育。绿芽的项目模式和农家女很像,都是通过与乡村本地妇女自组织合作来落实项目。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形式就是通过和乡村姐妹的合作,把儿童性教育带到她们的村庄去。
在项目上绿芽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当时我们跟谁合作,做什么样的预算,我都可以做主。每次和伙伴们聚在一起看到那些反馈数据,感到我们确实是在带来改变。通过农家女和绿芽的项目,我也认识了很多乡村姐妹,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和她们保持联系。
田野调研带来对于性教育本土化的思考
2019年,我和一个研究团队一起做了一次深入调研,在一个村庄做了几个月。我们发现,其实孩子们知道很多有关性、性别平等的知识,但是这些在学校学到知识、价值观,到底有多少能够转化为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当时我们跟踪调查的都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在ta们上过几节性教育课之后,我们给每个孩子一台相机,让ta们去拍生活中与“性”有关的内容。当时那几节性教育课都是我给孩子们上的,课堂反映很好,孩子们回答问题很积极,对知识的接受度也很高,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相机给到孩子,期望收回来的照片里会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孩子都刻意回避了一些东西。
在田野研究中,有时候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东西应该出现,但诡异地没出现。在我们跟踪调查的十几个孩子中,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去拍村子里贴的流产广告和性病广告,但那些广告其实就贴在ta们每天必须经过的地方,而且是明确和“性”有关的。我们让孩子拍自己家里的厕所、浴室等等,有些孩子也非常避讳。孩子们在后期的访谈中说道,ta们不拍是因为ta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不能拍的东西。这就是知识和ta的态度、行为之间的脱钩。

2019年田野调研后的照片展
我们所说的“性教育”,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在知识、态度和行为这三个维度对“性”和“性别”的态度。知识是最容易改变的,因为那些知识都非常简单。孩子只要认真听课,怎么样都能听得七七八八。但我们发现课程很难改变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因为孩子们有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背景,而ta们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ta对性、性别的态度和行为。
很多知识我们在学校都学过,比如说要“勤洗手、多锻炼”,要做一个“健康向上,好好学习,热情洋溢”的小孩。但实际上这些是“知识”,这些道理我们都懂的。但这些知识很难转化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性教育的实践中,不管我们在课堂上再怎么说“你可以讨论性,这是很正常的知识”。但是孩子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整个村庄的环境、别人的态度……都是一时改变不了的。孩子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那孩子们对性、性别到底会不会有我们希望的态度?可是,如果孩子们的行为不能体现自己的态度,你又怎么判断孩子们是真的形成了这样的态度,或者说孩子们未来会做出我们期待的行为呢?
我之前看过一本关于台湾地区开展性教育的书。作者写道:我们现在希望通过性教育实现的那个目标是一个非常所谓“健康”、“正常”的目标。我们希望孩子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和性有关的事情做决定;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能和伴侣维持正常的关系;能拥抱自己的多元性取向……这其实是非常西方、白人、中产的一种典型形象。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太“好”了。我开始质疑,这是不是我自己真正认可的一种价值观?我们是不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性教育让中国的孩子,包括乡村的孩子,都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尤其是把这样的“性教育”加入学校教育之中。因为学校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它有一套“标准”,它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符合这个标准。那一旦有一套标准,就肯定会有不符合标准的人。我开始怀疑这种标准化的、统一的、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明确目标的性教育,是不是真的那么站得住脚?
我们在乡村做性教育的时候发现,城市和乡村对性教育的需求真的不一样。联合国的研究发现,虽然全面性教育会使得安全性行为的比例上升,但有时候性教育可能会导致性行为年龄的提前。在城市做性教育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们不怕孩子的性行为年龄提前,只要ta们能进行安全地进行性行为就好。这句话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里可能是立得住脚的。但很多乡村孩子的真实状态是,ta们的性行为年龄本来就很早,ta们的性行为也是不安全的。这和ta们很早进入婚姻,很早生育有关。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想通过性教育促进ta们不怕提早性行为年龄,而是进行更安全的性行为,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错位的。有的时候我也思考这是不是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但是如果用“乡村的发展阶段还没有那么先进”来解释这种需求的不同,好像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城市里这些能理解这个所谓“标准”的人,才是正确的、文明的,而乡村里的这些人和孩子是未开化的。我很反感这种叙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取向。我还是相信,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通过性教育来实现我们讨论的这些目标,这真的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但我确实开始怀疑通过“学校教育”这种模式,尤其是通过推广“标准课程包”这种方式来推行性教育,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说是否真的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的。
我觉得我的思考肯定都还在很初级的阶段。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定论。可能我想的这些又都是错的,可能那种标准化的课程包推广也是一种很正确的途径。但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本土化,但回到哪里去?
本土化的实践还有另外一个陷阱,就是你要回到哪里去。西方那一套不可能完全照搬,公益行业的人也都赞成。但是你回到哪里去?你能回到传统中去吗?那些所谓的“传统”它又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我们做全面性教育的时候会有一些持保守价值观的人说“这一套不适合中国”。但是说这些话的人,ta们对于乡村的了解也是基于ta自己所处的角度。有一些乡村姐妹的村子是扶贫重点驻点村,有扶贫干部。我去她们村子的时候,也跟一些扶贫干部打过交道。一些扶贫干部ta们在村子里,但是实际上你觉得ta又不在村子里。网上有很多扶贫干部吐槽说“那些老百姓又穷又懒,重男轻女”。不是说这不该反思,但是ta们批判、反思的角度明显不是这个村子的一员。ta们只是来执行任务的,ta们也是带着一套标准想要来改造村子里的人。比如说你不能穷,你穷是不对的,你也不能太懒。你说ta们真的了解中国的农村吗?我不觉得。真的了解村子的还是村子里的人,是村委会的干部。到了“县”这个级别,我觉得真是不一定。
2021年河南水灾的时候我去做志愿者,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位女性。她在当地自己做生意,也有一个自己的妇女团队。第一次见面,她问我:“你大学生一年能赚多少钱?我去年一年赚了60万”。其实她是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吸引了一群乡村女性在她身边一起工作。这个妇女团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村庄或者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按照任何一个标准来说,她肯定都不是一个乡村发展者。这位姐妹她一方面很符合我们希望乡村妇女实现的一种状态;但在另外一方面,她的很多观念又是非常不符合我们希望乡村妇有的一种状态。
当我真的进入乡村,我发现妇女的赋权真是有不同的形态。我在公益圈儿做了快十年,居然还能说出这句话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儿,就好像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在公益圈做久了,也可能会有一些标准:就是你觉得孩子们应该是什么样,乡村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因为ta们可能是其他的模样,甚至和我们的期待南辕北辙,但是那仍然是一种发展的可能。
——张新宇

探访乡村姐妹途中
我现在更想要成为一个帮忙的人
2019年那次调研算是一个明确的分水岭。以前感觉还是很激情洋溢的,觉得自己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但那个研究真的对我造成了很大冲击。我现在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有定论,我也不再相信自己真的做出过很多贡献,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种感受。我有时候还挺怀念以前那种斗志昂扬的状态。但是没办法,我骗不了自己。
我现在不会说“我要去改变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要向大家传递什么样的知识”。以前我们经常会用的话语是:“我们要传递、帮助、普及、提升、改变”,但我现在更想要成为一个帮忙的人,真的是帮忙的人。我现在和很多乡村姐妹维系的一种关系是: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我就来帮你。就好像是这个团队的勤杂工。前段时间一个乡村姐妹要在村里组织调研,想要、也需要一些建议,她跟我说了,我就跟她聊。我会觉得这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心安理得的状态。也不能说这样我就是她们中间的一员了,因为大家在地理空间上,或者说在实际身处的境遇上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不是在打乱这个地方的生态,而是在辅助。
后来我就开始想,如果自己将来还做“妇女”或者“性别”这一块,我就不会再去做"赋权" 或者说"教育课程"。相反的,我会去研究不同地方的妇女自组织,去看她们有哪些应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工具去应对,有哪些实际的应对窍门。不管是自然灾害,性别不平等,还是暴力,甚至我可能会介绍这些自组织互相认识,去形成更大的团结。
我现在仍然会想起大学时候去社工系选课旁听的时候,办公室墙上写着“助人自助”四个字。当时大家不说“公益行业”,大家说的是“助人行业”。这是我对公益行业最初的了解。现在感觉反而是回归初心,去做一些很“具身性”的,身体能感受到的助人行为。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也是我要去做的事情。
讲述人:张新宇
访谈人、撰稿人:蒋雪玮
照片均由张新宇提供
播客片头音乐:Guitar, Acoustic, GMaj7 Chord.wav" by InspectorJ (www.jshaw.co.uk) of Freesound.org
播客片尾音乐:Electro-acoustic guitare loop in C dorian by matt141141 of Freesound.org